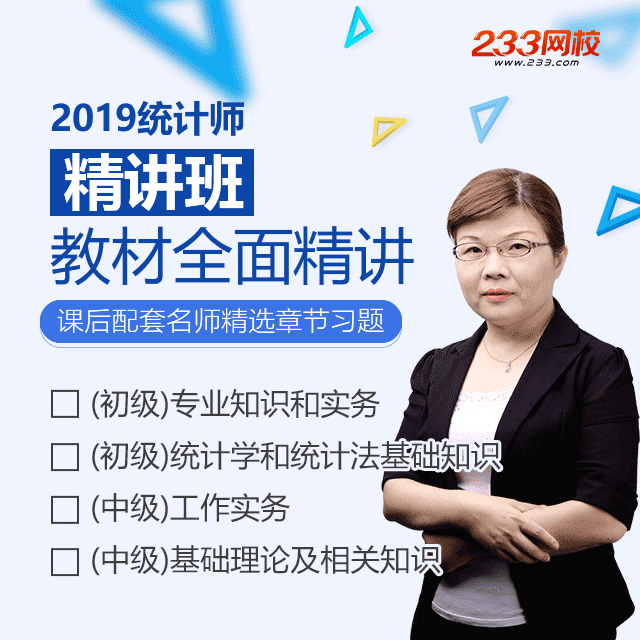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,拒绝活在统计学的梦魇里几乎是不可能的,这比拒绝工作还要匪夷所思,甚至于你可以拒绝活着,但你拒绝不了统计学。比如作为大学老师的我,每到年末领取绩效工资,都需要填写大量的表格,这些表格最终都可以简化为统计数据。比如发表了多少文章;申请到多少项目;获得什么奖项……
因此,文学深陷统计学的灾难很难被定义为“丑闻”,既然一切都要在生产和消费的层面上考量,那把文学和文学主体数字化,是再自然不过的。很久以前,雅斯贝斯就宣告,技术和机器已成为群众生活的决定因素,其核心价值是生产和分配的合理化,这一合理化的实现不是依据于“本能与欲望”,而是依据于“知识与计算”。况且,就像波德里亚所说的,统计是一种实现欲望的形式,绝大多数个体都渴望得到统计数据形成的合理化的优越位置。
比如,多数作家都无法摆脱统计学的引诱,看看他们的简介或者“传记”就会明白,完全被一种数字化的统计思维控制着,身份的确立和认同依赖于等级不一的统计标准;同样,统计学的引诱也即统计学的囚禁,作家们的焦虑也往往与统计数据密切关联。当然,学院学者就更是如此,在量化模式下,一切不能数字化的、超越于职业范畴之上的价值都是无效的,所谓学问因此不过是知识的一些极其封闭和丑陋的“简单再生产”,在它们身上寄托任何高贵和智慧的假想都将是愚蠢的。
在统计学形成的存在论里,人将消失,而数字立于不败之地,因为人早已经被规训为数字。而此时的数字,已经不是毕达哥拉斯(万物皆数)、柏拉图(造物主是数学家)、伽利略(宇宙是一部以数学语言写成的巨作)眼里那个形而上的、本体论色彩的数字,它服膺于资本主义的统计思维,变成了“葛朗台”、比尔·盖茨、巴特勒眼里的数字。这一切似乎难以抗拒,比如,如果在统计学的范畴内谈论文学是妄谈,意味着腐朽和堕落,那不在统计学的范畴内谈论文学呢?文学将消失,这和人的消失保持着一致性。
马克·吐温说:“世界上存在三种谎言:一是谎言,二是该死的谎言,三是统计数据。”没有统计学就没有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,但他在论述“机器和大工业”的时候明确指出:“不论在什么地方,想要不掺假的统计材料都是很困难的。”所以,本质上讲,统计学没有真假之分,信与不信,也并非那么泾渭分明;反正你只要活着就无法离开统计学,当然死后也无例外。
威尔斯(H·G·WELLS)多年前宣称:“统计思维总有一天会像读与写一样成为一个有效率公民的必备能力。”在一个全民拜金的大时代,这一预言已经提前实现了,我们的作家、艺术家们也早已和商人、政客一样,学会在睡觉前摘下面具,统计一下银行卡上的余额,然后做个好梦。
相关推荐:统计师行业聚焦